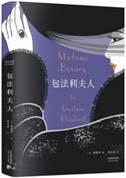|
|
|
女性零余者 ——《包法利夫人》书评 儒学高等研究院 任煜
19世纪的俄国,一群愤恨现实、出身于贵族的知识分子虽对自身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始终跨不出虚浮思想的藩篱,缺乏切实的行动和勇气,进而无路可走,以此终了一生。具有这样典型特质的人被称为“零余者”,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描绘的毕乔林,都是这类形象的典型代表。 《包法利夫人》作为一部以女性为第一主人公的小说,竭力以冷静、客观、不留情面的笔触来解剖爱玛,还原爱玛生活、思想上的真实性,并同时呈现出了一定意义上的零余者的某些特征。作为一个乡下女孩,爱玛得到了意外的机会进入修道院学习贵族礼仪,她和自身原本身份面貌的心理差距感也由此而生。虽说学得了书画礼仪,懂得了优雅气质、举止脱俗,但这些却始终是镜中花、水中月,虚幻而又缥缈,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爱玛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思索。正如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中所说:“常年无所事事,幽闭的栅栏刺激想象……有的姑娘,由于过去耽于空想,就要引起一些多少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误会。”爱玛此时尚未结婚,有的尽是小姑娘的爱情幻想,美好、刺激、兴奋、令人神往。但和包法利先生结婚之后,所有的期望全部落空,这个女性便开始了自我精神上的无限思量和疑问。 不同于典型的“零余者”,作为非贵族阶级的女性,爱玛所进行的思想探索只能说是为了自我满足和幸福的。她的苦恼在于找不到不可思议的、令人迷幻的爱情的出路,她依附男人,依附丈夫查理·包法利,因为曾给过她爱情的希望却又很快在现实生活中破灭;依附情人罗道尔弗,有了肉体的放纵和欢愉却又很快厌倦;依附情人赖昂可只能凭借假想来延续热情。爱玛的所有渴求都是要求有实际的作用、实在的好处的。在女性受限的时代里,她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得到爱情,脱离女性的狭小世界,让男子来启发她、引导她,领略一切生命的奥秘和闻所未闻的全部欢愉。讽刺的是,她的脚步始终在道特、鲁昂、永镇这几个小城镇里徘徊。她生活的世界注定狭小,也注定逃不过狭小世界里的庸俗鄙陋。 天性多感,也就是后来提到的“包法利主义”让爱玛有了一种神奇的本领。她在思想的广阔领域里完全把自己设想成另一种样子:灰暗人生的稀有理想,庸人永远达不到,她觉得自己高于庸人,一下子达到了这种境界。殊不知,她仍旧只是个生活和思想上的庸人而已。 奇怪的是,凭借着这种异想天开的设想能力,爱玛是时刻充满希望的,只是她这希望太不纯粹,包含了太多杂质。她热狂而又实际,混淆物质感受和精神愉悦,她渴望脱离生活地界的狭小单调,却又最终落入思想境地的狭窄、鄙陋。她进行思索,不为别的只为自身;她因思索而愈发感到痛苦,找不到书中描绘的欢愉、迷恋、热情这些字眼,进而终于丧失一切希望,服毒自杀。 成为包法利夫人,可能是爱玛悲剧的源头。她始终把希望寄托在男子身上,将爱情当做全部的生活内容。她苦苦地为了爱情而爱情,出于自身的受限,她注定生活得狭小而又庸俗,她的悲剧,只能说是再普通不过的现实生活罢了。
好书推荐:《包法利夫人》 索书号:I565.44/104 内容梗概:《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这里写的是一个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很常见的桃色事件,但是作者的笔触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爱玛的死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努力地找寻着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